1980年立春刚过,黄土高原的盐碱地还凝着霜花,我在漏风的土坯房里出生。
接生的是邻村赤脚医生刘二婶,她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,用豁口陶盆里的温水潦草洗了把我的身子。
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,烟锅里的火星子忽明忽暗,像极了村口那盏总被风刮灭的油灯。
母亲产后第三天就下炕,背着我赤脚蹚过结冰的河沟去借粮,河滩上的碎冰碴子划破她冻疮溃烂的脚掌,血珠渗进冰面,凝成一串暗红的梅花。
屋梁上悬着两串蒜辫,那是全家唯一能变钱的物件。
春天盐碱地泛白,父亲佝偻的脊背总与犁铧构成锐角,他的裤脚永远沾着碱土结成的硬壳,像套着副泥铸的镣铐。
六岁那年,我趴在漏雨的教室补纳鞋底——那双露着大脚趾的千层底,是母亲用村里丧事捡来的白布染黑缝制的。
课本里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铅字被雨水洇成墨团时,我正偷啃从同桌书包里摸出的半块玉米饼,饼渣掉在《自然》课本插图上,盖住了画里丰收的麦田。
腊月二十三祭灶,村长儿子开着吉普车碾过我家麦田,车轮卷起的土块砸碎了腌咸菜的粗陶瓮。
父亲把烟袋锅往磨盘上重重一磕:“考不上中专就别回来!”
那年村里唯一考上师范的春生哥,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回乡,胸前的钢笔在阳光下反光,晃得父亲眯起眼。
母亲连夜拆了陪嫁的缎面被,给我缝了个装课本的布袋,针脚歪斜如蚯蚓,却绣了朵并蒂莲。
初中开学那天,我在操场被城里的孩子当牲口围观。
他们戳着我露出棉絮的袄袖哄笑:“扶贫办的活广告!”
班主任捏着鼻子收下学费——三张皱巴巴的拾元钞裹着二十斤黄豆,豆粒间还混着母亲纳鞋底时掉的头发。
物理课讲到“摩擦力”,我盯着黑板上的公式发呆,耳边却响着父亲咳喘的痰音。
他肺里的积尘比盐碱地的土还厚,却坚持不用那瓶止咳糖浆:“留着,等你考上中专送礼用。
1995年夏末,我攥着专科录取通知书站在村口,身后是塌了半边的土坯房。
父亲蹲在柿子树下磨镰刀,刀刃刮过磨石的声音像钝锯子割木头:“保安学校?
看大门的营生还要念书?”
母亲把蒜辫全卖了,凑出三百块钱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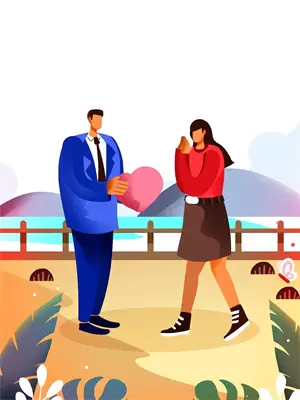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